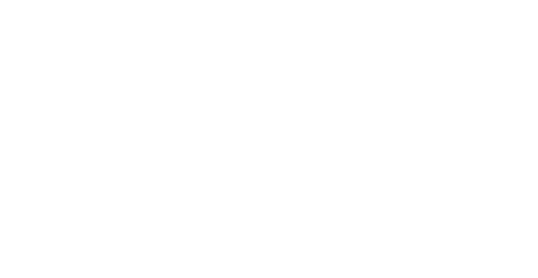从苏武到洪皓——民族的雁南飞
9282110
2017-02-21

一
当肃慎民族从贝加尔湖畔动身,跨越六千年的漫长跋涉宣告启程了。
这群漫漫南飞的大雁,飞过浅草接空的无边萧瑟,耗费千年,终于找到放马养鹿的栖息之地,他们在我国广袤的东北地区落脚,长白山旁升起忽闪的火苗,于此合翼,以此为家。绵延到北宋末年,他们才算真正站立,告别肃慎、挹娄、勿吉、靺鞨的称呼,以金国的形态,出现在中国地图。
早在孔子口中,透露了他们的不易。中原早就进入青铜社会时,他们连那射猎的箭镞,还停留在用石块打磨的笨拙时代。孔子若知道这个异族早前的悲壮长征,会有什么想法?
很多文化,都在迫不得已中出生,在茫然无措中探索,为了更好的局面改造自身适应。民族思维和生活习俗并不容易变动,在与异质文明交汇时,民族本位的想法使双方都怒气冲冲,都那么不甘心。
对抗异族的爱国之士振臂了,满腔激情的家国诗文吟诵了。他们在过去和未来的岔路口,从各自的立足点出发,展示着人类分割成若干群体矛盾冲突和群体追求的情感选择之痛,战火中冲锋呐喊,谱就悲壮之歌。有血有泪的选择冲突,印证着人的价值,民族的价值,为我们留下历史进步中需要反省的细节。踏进那块地方,才看见许多民族跋涉与冲撞之间的感动。
许多个人因为这场狭路相逢,遭遇凄婉,他们也像极穹庐中阵阵鸿雁,为了各自的生存家园,捎带希望与留恋,飞向天空另一边。
二
贝加尔湖送走肃慎后,迎来让中国头疼一千年的匈奴,这是第二个见证它美丽的民族。
大漠是游牧者的天堂,生来血性,生来血腥,生来天然,生来勇力,这种环境下匹配了一股股强劲的战斗力。因为气候一年比一年冷,马匹牲畜的粮草青黄不接,他们迫不得已,大部分部落向温暖的南方迁移。雁南飞,雁南飞。
大漠深处,马是唯一的丈夫。它们驰骋百里,围逐猎物感到疲累,就在这无垠的湖边饮水休息。它们知道,眼前的这片水域,被南方遥远的汉朝称之为北海。
不久,贝加尔湖有了第三个民族代表的陪伴,然而这里的风光并不令他神清气爽。
他是汉族人,苏武。
前100年,苏武以使臣身份来到大漠。汉匈本已停战,但没有减少磕绊,因为匈奴的一场内乱,牵连到了苏武头上。汉朝降臣卫律威逼,匈奴人利诱,都想使其投降,却均没有奏效,索性把他扔到北海放羊,吃吃苦头。
苏武来到这儿身已重伤。他曾被匈奴人困在土窖,餐雪食毡,侥幸不死,被他们看做神仙。既是神仙,那就等到公羊生崽,你才离开北海吧。
山边松树,身后羊群,脚下野草,太阳挂在天南,落山也比大汉早太多。深邃的海倚靠平远的山,故国虽有内灾,却不至于无炊食,可北海什么也没有,他一度刨开野鼠的储藏,以野果果腹。卫律所云以身沃野,看来真的要如此了。
海边野山坡,苏武牧羊地。这个苍老的男子,手持汉朝符节,驱赶匈奴羊群,倒有点像堂吉诃德了。那个骑士还有孤独的远方可走,苏武只能困蹇于此。一阵寒风,鬓发凌乱,符节脱落的毛也落没羊身。尽管它渐渐光秃,却是苏武唯一支撑的理由——他是大汉的代表,两个民族的枢纽。那柄符节的锦绣被脱落,无关长安风,不在大汉土。
这样一比,让李陵低下头来。他和苏武故交,被派遣来到北海设酒席款待苏武,也是为了劝降。以自身为例分析苏武,他却一如既往,不为所动。李陵羞愧离开时,仰天长叹苏武的忠义,自己和卫律的罪过通天。
其实,李陵何尝不无奈?大雁欲飞之际,栖身之地已被武帝毁坏。大动荡下的政治劫难,本身已被拷问,那是错综的困局,困在异族与国民中。
南方政治绝情时,北海闪出一粒温暖的火光。
那一天,单于的弟弟於靬王打猎至此,见到了正在牧羊的苏武。苏武帮助他打猎,相谈甚欢。此后,他派人送去许多用品,极大改善穷困生活。直到於靬王病重的时候,还给苏武送去了马匹、酒器、毡帐等物。
一个人在病重之际也没有忘记馈赠敌国使臣用物的事迹,可惜在很多现代史家眼里当做可有可无的材料忽略了,这很让人失望。要知道,那些物资对于本族的任何一人,都有极大的帮助。若以他们的视角,这个可有可无之人,该是在海风中奄奄枯朽的苏武了。
於靬王做到了匈奴为数不多的觉醒,他在和诸多汉文化交接中,老人海边牧羊的形象下,剖析匈奴迁徙他方,苏武万里投荒时,一定感受到了人类跋涉的某种真相。尽管其他的王不会厚待,但他仍然做着自己的守护。我们知道,守护得越久,等待的才有可能来到。
等待,意味着煎熬。苏武循环地活着,坐山,放羊,听风,看海。海边大多是长青的松杉,只有积雪的荒草,古怪的太阳,越发干枯的脸,他才能感受到时间一滴一滴的变化。
过了几年,听到武帝驾崩的消息,他意识到,符节将折了。面朝南方,吐血而哭,早晚吊丧,尽臣子之义。
坐山,放羊,听风,看海……
终于,在北方的第十九个年头,有一只鸿雁从贝加尔湖畔起飞,南度万里荒野,经长安城上林苑,被汉昭帝射落,上有书信,写着苏武的消息。
——这是昭帝刘弗陵编织的童话。这个童话真好,它把每个人渴望幸福的痛苦、家人期盼游子归来的心理处境和现实处境完美展现出来了。这只鸿雁,可以是个人,也可以是群体,它从酷寒而来,到温暖栖止,人们感受它的渴望,往往以让它受伤的方式展开。
终于,渺无希望之后,苏武等到了消息,他要离开这个留守太久的地方了。
出发前,李陵送行。剑舞而歌,歌曰:
径万里兮度沙幕,为君将兮奋匈奴。
路穷绝兮矢刃摧,士众灭兮名已聩。
老母已死,虽欲报恩将安归!
泪下数行,诀别。七年后,这个被苏武赞为“才为世英,器为时出”的降将,孤死他乡。雁南飞,雁南飞。
十九年的漫长时光,苏武归来了,承载着大漠北海的艰苦归来,坚守着中原大地的信念归来。此时,两个民族的辛酸,染白了他的须发。

三
肃慎人无缘在北海看见苏武,他们流浪东北千年,在南下与宋周旋的时期,见到了另一个宁死不低的头颅。
他叫洪皓,《容斋随笔》作者洪迈的父亲。
两宋之际,宋弱金强,在金人扶持下,刘豫的伪齐政权建立起来。洪皓作为通问使臣派往北方,自然不受欢迎。完颜宗翰让他在刘豫那里做降臣,他却一身傲骨。几经周转,被押送到距离金国上京百里的冷山(今吉林农安)。这个地方在唐朝属安东都护府管辖,松漠都督府治理。
相比苏武的北海,这儿也好不到哪去。地处寒带,细草到了四月,才从皑皑白雪中探出脑袋,人们和干脆学着碎草穴地而居,以最落后的方式抵御严酷的恶境。
北风卷地白草折,胡天八月即飞雪,东北也一样。洪皓初来,曾以马粪为柴草,烧开难咽的草食。大雪封山了,这个汉族人回到最初的人的身份,和女真族一道,在艰苦中生存。
金国陈王完颜希尹欲取四川,向洪皓取策。洪皓却道出四川防御工事的完备,你是在玩火自焚。完颜希尹大怒,一个俘虏之臣,在这样窘迫的境地还如此嘴硬!洪皓对这个人的怒气,反而格外平静:“既是北方的俘虏,你把我干脆投入井中,向外说是我自己失足跌水而死。”洪皓替完颜希尹想好了制裁手段,等待死亡,可这一番视死如归的话,却感染了他的恻隐,心生钦佩。
洪皓开始教完颜希尹的八个儿子读书,育穷困的冷山人民学习汉文化。那时,冷山无纸,洪皓和女真族人一起拾拣桦叶,以叶为纸,写下孔孟文章。
一片片树叶,留下文化塑造的艰辛;哒哒的马蹄,覆盖枢纽传导的音响。最初的开拓者总包围在野蛮的障碍,当岁月和凄苦厮磨出白山黑水的云烟,总算在跨越文化冲突后寻觅到最佳涉足点,斡旋有了惊人定力,获得了所有人的尊重。
有了尊重,就有了力度。马上,完颜希尹还会向洪皓继续学习先进传统,把汉族文化制度向金熙宗谏言,结合唐、宋、辽和本国实际制定规章,使金国改掉国论勃极烈制度,换为三省六部制,汉化之路再次缩短。
我们以汉族本位的思维,谴责完颜希尹谋划掳走宋徽宗、宋钦宗,但在遇到民族融合的许多人类学命题后,一切都变了样。诡怪的是,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,都有出自忧患的心理意识。阴惨和明丽,都在融合枢纽期中荡开,熨成共跻伟大的人物,同属壮烈的悲剧。
洪皓会想到千年前苏武的孤独,他却在这片文明的荒野中额外收获了一叠叠军事情报,塞进罅隙托寄南国。当然,还有许多大宋臣子勾结金国的秘密,洪皓眼前铺陈出一团繁乱。这种乱贯穿了洪皓一生,尤其是在这里的停留,更加显豁,更加危险。
寒漠十五年,冷山、云中踏遍。金熙宗得子,因为大赦天下的契机,洪皓驾起快马,奔突向南。虽然金国有人反悔,可是归心似箭,哪里追的上?雁南飞,雁南飞。
黄河白马渡,收辔停驻。他已十五年未见这条滔滔长河,现在终于可以稍作休整,观望一番。这是一条分界线,过了这条线,就到了梦魂所归的汴京。残山破河,仍是吾乡。
民族兴衰的万千感触,聚于心头作悲歌:
国步日多事,霜露任沾衣,
留落十五年,至今方北归。
夜投胙城宿,百里即王畿,
遥望一惆怅,何当拜天威。
直到宋高宗见到他,称之为苏武再世。
洪皓重新起草北国见闻,编为《松漠纪闻》一书,成为研究金国人文风俗不可缺少的文献。
历史文化的积淀,在融合时期会产生民族的沙文主义。摒除偏执的民族观,才听得到贫瘠中的生存呐喊,那是迫不得已的选择,无奈纠葛下必然的多余。洪皓在那里生活的十多年,把一个民族的困境,用刚正宽厚的汉族文化做了治疗。
谁能想到,那里的国家之爱,会得到另一种结果呢?
他曾在北方探知秦桧勾结的事实,成了宰相的威胁。从极北归来四年后,被贬向遥远的岭南,谪于英州(今广东英德),直到秦桧重病,翻案北归。只是,连年苦寒与岭南湿热的艰苦生活,这时已身染重病。走不动,出发没多久便溘然长辞。就在第二天,秦桧也去世了。

四
苏武从北海飞到长安,洪皓从冷山飞到汴京,他们悬着的心才算落下。在他们生前身后,有太多怪异的声音,对历史的不公嘶哑诉苦。
肃慎从贝加尔湖飞到黑龙江,匈奴在漠北草原辗转翱翔,都是一直被汉族人怪异的称呼着,民族群体的分散合流,有多少对方眼中细节的公正剖析?
人类以局促的眼光掩住了进程本质,心理上的自我防范和他人对垒,产生了无尽的障碍。来自各个层级的不同应对方式,跋涉与交汇的真相,也在扑朔迷离中混沌。血光折剑下,并没有多少的武为止戈而动,更多的牺牲,并非来自异族的入侵和抵抗,而是源于机诈的固我,偏偏这种心理又是长期观察社会之后,出于必须的考量。文化考验着民族,同样也被自身的容量所考验。这种诡怪的漩涡一旦构成,开始发挥能量,距离群体本身诉求的温暖之地,也就背道而驰,变得越来越远。
地球是圆的,鸿雁即便向北飞,它也能在最后接近温暖。可是,它并不能保证经受霜雪后的完整。无论顺路还是顶风,总会有掉队,极端选择极可能使集体消声匿迹,湮于尘埃汪洋。
苏武和洪皓,同属中国文化代表。我们当然可以很骄傲地认为中国文化精神距离一千余年,仍然可以经受住少数民族的绝地考验,但不能对边走边学其他民族的事实置若罔闻。
中国历史,何尝不是一部文明融合史?从遥远的原始社会慢慢飞起,流着先祖的泪,洒着自己的汗,渡海越山,艰难的跋涉,飞向温暖的南方。我们局限于自身的时空,在回顾中漫漫摸索,体验着复杂文化结构下的创造、觊觎、争执、守护、共享,方式也多重多样。从这些使者身上,我们感受到不光是本民族的苦涩,还有那些古老民族的艰难挣扎。
天苍茫,雁何往?它们在斜阳秋空有过不同的嗥声,远方栖所确是群团的夙愿。因为长雁远去只留下永久无痕的苍凉,但愿路上少一点弋射,多一点共仰;少一点推搡,多一点互帮。
也只能是祈愿而已。
进入圈子
|相关推荐
|讨论区

暂无数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