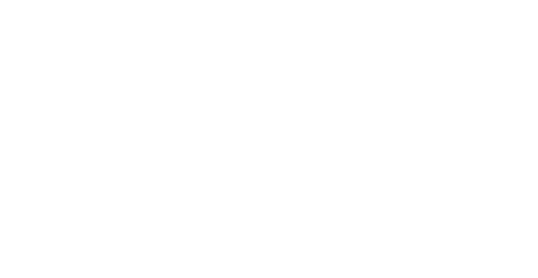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一本书能让成年人掉眼泪,曹文轩的《草房子》却让我不止一次湿了眼眶。
第一次读到《草房子》时,我还在这个城市的一个小学里当孩子王。为了表达这本书给我的感动,我跑遍大半个京城,从十余家书铺里搜齐了42本《草房子》,在毕业典礼那天送给我的孩子们。他们跟了我一年,彼此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我用这本书完成了与孩子们的告别,也结束了我今生第一次的教学生涯。
岁月已经老去,情感依旧鲜活。我想《草房子》就是用“从前”岁月里少年的朦胧与忧郁、温情与哀怨勾起了沉在人内心最底层的感动。每次想到“草房子”这三个字,我的心都好像被故乡老母亲冲的红糖水滋润着、熨烫着,许多回忆像风后水面的波纹轻轻地散开,最后又了无痕迹。

书中桑桑和纸月那种少男少女间毫无瑕疵的纯情最是让人感动。一个少年对女孩子的喜爱表达虽然多种多样但大都包含了调皮、胆怯、逞强……害怕直接接触却又时时挖空心思地想引起对方的注意。喜悦与忧伤都积淀在少年朦胧的片断里。
小学时,跟我最要好的朋友小果喜欢上一个同班姓董的女孩。小果人高马大但学习不好,因常常抄我的作业而对我充满了感激。他喜欢那个女孩的事是一个公开的秘密,课间玩耍时他常常把别的男孩撞倒在那个女孩的脚下,然后又极有风度地把男孩拉起来。如果哪天那个女孩多看他一眼,课上他都会笑出声来。
这样的回忆让我想起桑桑为了吸引纸月的目光,夏天穿着大棉袄在操场上走来走去;想起桑桑为了纸月不被欺负,悄悄起个大早去打架。小果后来终于等不及,有一天偷偷问我“董”字怎么写,我写在一张纸上递给他。中午放学时,大家都发现土教室前的白杨树上贴着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“董某某针票凉(真漂亮)。”
所有围观的孩子笑炸了营,那个女孩脸红得掉下泪来,快速跑开了。下午老师没费什么劲就把小果查了出来,我也被叫到办公室,老师问我是不是帮小果了,我说没有。老师说凭小果的“针票凉”绝对不会写对“董”字。小果承认“董”字是我教给他的,但整个事件跟我没关系。虽然如此,我们俩还是被罚站了整整一个下午。之后老师带着小果去跟那个女孩道歉,小果走到女孩跟前小声说:“对不起,我不该说你真漂亮。”
女孩笑了,全班也都善意地笑了。去年我回老家过年,小果和姓董的女子真得结婚了。他听说我回老家了,拉我去新房喝了一晚上的酒。说到那个被罚站的下午,小两口都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《草房子》给你的美感就是常常带你到梦一样的氛围里,那些散落在竹丛与杂花间的草房子,那个被河汊与荷花包围着的校园,充满了无尽的情趣与诗意。在桑桑并不连贯的印象里,野草丛散满了神秘,河水流淌着淡淡的忧伤。纸月似画,杜小康如诗,细马和秃鹤更怀了俊美少年的梦。甚至连桑桑自己的病难都在淡雅的文字中透着温馨的色彩。
说到病难,我有深切的体会。由于自小瘦弱,常常被父亲用车载着去看各种各样的医生。第一个本命年的那个春天,跟桑桑类似,我的脖子右侧长出了一个红疙瘩,初时很小,越来越红肿。父亲带着我走遍了附近的大小医院,打了无数的消炎针,吃了数不清的消炎药,都没有结果。不知从哪里得到一个偏方,说要用黄连根和茅草根煮水,一遍一遍地热敷。
父亲便每天背着筐到野地里寻黄连树、挖茅草根,但效果甚微。后来终于打听到六十里外的西乡有一个姓陈的老先生最会看疮,父亲用车载了我天不亮就去了。由于我的脖子疼,不能受到震动,父亲看到路不平时就下车推着我,这样骑骑推推,推推骑骑,一直到中午才到。
老先生看了看,说:不过是大点儿的火疖子,不碍事。老先生用刀割开肉皮,把里面的脏东西很仔细地挤出来,把一个蘸了药沫的棉球塞了进去,包扎好。又给了两包普通的消炎药。说七天后就有效,但要隔七天来换一次药,坚持七周就好了。父亲连声感谢,要给他钱,老先生坚决不收,说药粉都是自己做的,没什么费钱的地方。七天后红肿果然消退不少,年逾花甲的父亲笑得竟像一个孩子。
第二次去看时,给老先生带了许多烟酒点心。没等七遍药换完,我的病已然痊愈。但前后将近半年的折磨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了生命的磨难。十几年过去,那个老先生不知还在不在人世,如果在,也一定老得不能再老了。

回望过去,每一个人的回忆都是不连贯的,然而在那些近乎支离破碎的片断里,喜乐是美,忧伤是美,欢聚是美,离别也是美,甚至连同印在脑海里的病难也都充满了美的特质。
曹文轩说:“那里的每一粒沙尘,每一个场景,每一个人物都是可以进入到文学世界去的。”在喧嚣的都市里,读一读《草房子》,想一想乡野纯净的天下,微风翻卷着荷叶,又把清香吹得四处飘散,懵懂的少年奔跑在夕阳里,那少年是你,是我,是我们心底永恒的美丽……
《草房子》